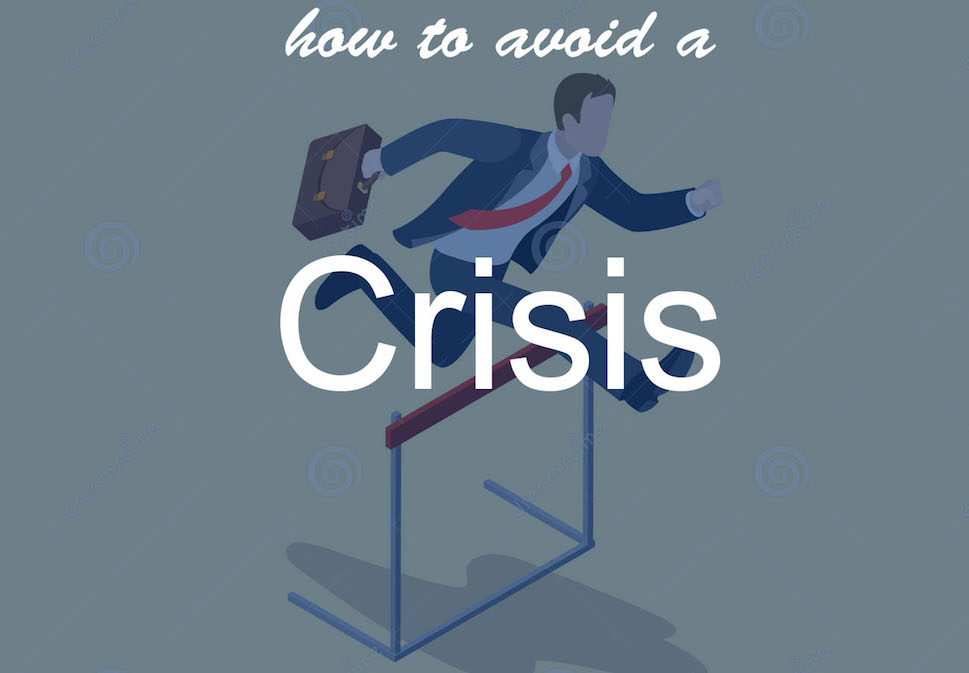如果商业是生活,购并是电影大片,则大公司之间的购并,绝对是这些大片中的高潮。这场高潮中,不同的企业领导人有不同的角色定位的选择。聪明的领导人知道这只是一场迟早要落幕的商业大戏,所以不忘记自己导演的位置,懂得调度和利用购并带来的大众和媒体的关注来增加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关键时刻大喊一声“停”,回到现实。另外一些领导人却往往忍不住自己充当主角的欲望,一心沉浸到闪光灯、聚光灯和封面故事的报道中去,以至于真把自己当作了旷世英雄,把一把纸糊的青龙堰月刀从台上一直扛到了家。这结果将是什么,大家自然可以想见。
对父母的爱缺乏信心的小孩往往容易有一种“注意力焦虑”的症状,大人的注意力只要几分钟没有集中在他们那里,他们就要想办法,使用一些儿童的小诡计来吸引大人的注意力。我一直怀疑,那种老想自己做主角、特别是做购并大片的主角的企业领导人是不是就是这种患有注意力焦虑症的小孩长大的。这种出于自我表现、自我膨胀的心理目的而进行的购并行为,在经济学、战略上有一个专业术语,叫empire-building。可惜一把瘾过完之后,不管主角愿不愿意,是戏总是要收场的,鼓息旗堰之后,灯火阑珊处,我们于是总能看见那个卸了妆之后有几分憔悴、又有几分落寞的熟悉脸孔。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激动人心的大片,,这些年一直没有断过,其中最引人入胜的,依我看来,恐怕得数奔驰购并克莱斯勒案(1998),GE购并霍尼韦尔案(2001,因欧盟反对,未成功),以及惠普购并康柏案(2001)。这几部大片的特点是,都有一个自我膨胀CEO:奔驰是施伦普(Jurgen Schrempp), G}是韦尔奇,惠普是不爱红妆爱武装、阳刚之气不让须眉的费奥瑞娜。施伦普和韦尔奇相同之处是两个人都在电影的最高潮处与结婚了几十年的老妻离了婚,换了一个更年轻的新妇。施伦普与费奥瑞娜的相同之处是,因为购并整合的失败,最近纷纷都下了台;而且,两人执政期间,公司的估价都损失了大概50%左右,大大超过了他们买人的公司的市值(等于什么也没买)。两人宣布下台时,两个公司的股价分别上升了10%和15%。看起来,股东们等待这两个主角“洗了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主要出于企业领导人自我膨胀的公已理需求而发动的购并,无论当事人如何把协同增效的道理讲得头头是道,到头来一场空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在这种心理需求的控制下,购并方在整合的过程中势必无法摆脱一种把被购并方作为战利品来看待的心理定势,从而势必在整合的过程无法真正贯彻“平等、尊重、信任、合作、分享”的十字原则,其结果是各种难于控制的局面,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彻底崩盘。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这个分析框架来看,被购并方的物质资本的转移问题不大,而人力资本(专利、技术、诀窍)的转移就有可能发生很大的风险,但最大的风险则来自社会资本的转移,包括员工对企业的信任(企业文化)_,顾客对企业的信任(渠道资源与品牌资产),股东对企业的信任(投资者关系)、合作伙伴对企业的信任和社区对企业的信任五个方面的社会资本。而这五种社会资本中,员工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基础。这里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两个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之中的资本,要实现它的转移,需要一个迅速重建信任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体之间通过最广泛的沟通、参与、互动,完成一个试探、印证、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稍有不慎,在被购并方员工焦虑、不安、不平中,被购并企业的社会资本就会像水银泄地一样,瞬息流失于无形。而且,越是知识密集型、品牌密集型企业,社会资本的含量在企业总价值中分量就越重。
所以,如果把签合同比作是结婚仪式,签完合同之后的整合,对于员工而言,其实就像谈恋爱。购并的问题在于,大多数购并往往是先结婚,后谈恋爱(而且出于保密的需求,往往还是秘密结婚)。虽然已经结了婚,但谈恋爱仍是要两情相愿,要花前月下,要山盟海誓。若一方非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对方,则强扭的瓜不甜,家庭生活肯定幸福不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良性的整合,只要被购并方还有一定的实力,就必须是一个平等、双向、有机融合的过程,不存在谁整合谁的问题;如果购并者把自己当作征服者,居高临下地把被购并方当做整合约对象,摆出一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的架势,这出发点首先就大错特错了。
奔驰与克莱斯勒的整合,很不幸就成了这样一个把被购并方当做为整合对象的典型例子。汽车作为传统行业,与惠普购并康柏等高科技行业相比,整合问题本身应该并不是特别严重。但这里多了一个跨文化整合的问题:克莱斯勒人这次要面对的可是伟大的德国商业领袖施伦普先生。今年60岁的施伦普的职业发展道路是典型的德国式的:16岁以技工学徒身份加人奔驰公司,从南非、美国到德国,一路提升,一直到1995年成为公司的一把手。施伦普的梦想是把奔驰公司变成欧、亚、美三足鼎立的全球性汽车公司。第一个目标首先是美国。经过三年的软磨硬泡,施伦普终于以“平等合并”的名义把克莱斯勒揽人怀中。可惜,他的所谓“平等合并”只是说说而已,斯图亚特开往底特律的公务机上,从此坐满了奔驰公司的德国高级管理人员,原克莱斯勒的高管人员只好纷纷作鸟兽散,新的组织机构图中,布满了德国人的名字。《底特律新闻报》记者撰写的《搭便车:奔驰是如何把克莱斯勒带走的》一书中这样记述2000年克莱斯勒加拿大籍总裁Jim Holdea的怨言:
如果你给我的职位做一个招聘广告,你可能一个电话都接不到!招聘:一家营业额720亿(美元)的生产性公司的CEO。财务部向斯图亚特汇报;公关部向斯图亚特汇报;采购部向斯图亚特汇报;没有(汽车消费)信用部门,没有CFO。请向斯图亚特咨询有关事宜。这样的管理架构,你怎么有可能伸展拳脚呢?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施伦普在回答《财富》杂志的汽车专业记者Alex Taylor关于这次购并的访谈时的一番表白:
你也许会感到惊奇: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跟我原来预想的完全一样,一点不同都没有。这也许就是我还是一个不错的棋手的原因。我们在(底特律)奥本山负责克莱斯勒的Jim holden非常出色。克莱斯勒与奔驰的高管人员已经开始对话了······大家非常有默契,这一直是我想要的东西……我与强势的人相处没有问题。Jim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为自己的想法辩护。如果强势的人有能力,并且很专业,我便会敬爱他们。
2000年年底,克莱斯勒营业利润比上一年度下降了90% 。施伦普“敬爱”的Jim Holden丢掉了他的工作,消息一时震动了整个底特律:德国人这下是彻底当家了!从2001年到2003年,克莱斯勒一直是巨亏,成为了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的一个无底洞。忙中出乱,更滑稽的是,爱做秀的施伦普先生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竟然对记者说,他其实一直都是想把克莱斯勒变成新公司的一个部门,所谓“平等合并”,只是一个解决对方心理障碍的一种美其名曰的说法。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曾是克莱斯勒最大单一股东的Kirk Kerkorian依此起诉施伦普和奔驰公司诈骗!Kerkorian是赌城拉斯韦加斯的主要发展商,当年曾伙同李·艾科卡搞了场未遂的MBO,当然不是省油的灯。要不是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多方周旋,法庭终于判他们胜诉,这场面还不知有多难看。
自我膨胀的逻辑结果是自我爆炸,施伦普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中国的企业家个人再自大,估计还没有到施伦普先生那样,需要到世界上去显摆的程度。但中国的企业家无法避免的却是一种是把自己当民族工业代言人、中国企业家阶层代言人的倾向,一脸国家振兴、义不容辞,我不担当、谁来担当的深沉状。从吸引看客的角度,这种姿态虽然容易出彩,其本质其实还是一种自我膨胀。而且,个人层面的自我膨胀只是企业领导人的问题,而集体层面的自我膨胀,往往比个人层面的自我膨胀更可怕。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收购美国企业,便是前车之鉴。还是那句话,在商言商,生意就是生意,要遵循生意本身的客观规律。千万不要让振奋民族自尊心、之类的非商业目标迷住了眼睛。联想当初购并IBM时,大力挡住“谁购并谁”之类的坊间议论,把CEO的位置让给一个美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确实是神来之笔! (来源:纸上谈兵说管理)
【战略】谁整合谁,这是购并的首要问题
- 作者: 超级管理员
- 时间: 2014-10-15 12:54:10
- 点击率: 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