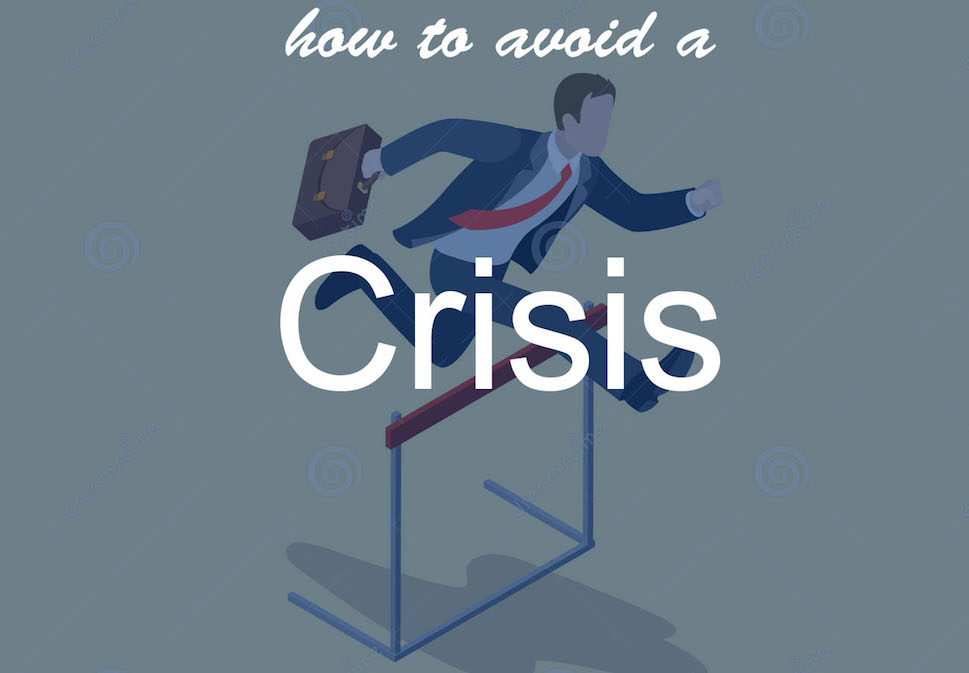跨文化专家黄伟东先生专访
谁也没有想到在跨文化沟通中如此游刃有余的黄伟东先生,回忆起自己当年为什么偏偏对跨文化特别感兴趣的时候,居然用了“煎熬”这个词。“是的,那真的是一种煎熬,是一种冲击。面对着完全不同于自己国家的文化,也许你最初会有一种类似于蜜月期的兴奋和喜悦,可是慢慢地这种新奇的兴奋褪去了。你开始被一种不知所措的沮丧所笼罩,更甚至,你会觉得痛苦。那就像是把你放在滚烫的油锅中煎来煎去的苦难折磨,这种感觉让你难以名状,你只是想着你必须要摆脱这样的煎熬和痛苦。”于是,我们的跨文化专家黄伟东先生就这样一边煎熬着一边收获着。时至今日十多年过去了,这位当时感受到冲击和煎熬的“很中国人的中国人”,终于可以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脸上露出微微的笑容,谈笑风生地告诉我们怎样可以在跨文化中做到像他今天一样的游刃有余。
煎熬在“文化休克”和“重返本土文化休克”中
黄先生在海外生活和工作很多年了,现定居北京,经营着一家从事跨文化管理咨询和培训的公司。他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航班已经不计其数,其中有两次回到北京的经历最让他难忘。一次是1996年在美国生活几年后初回北京,一次是1998年返回美国后又于2001年底再次回国。之间的五年时间差距让黄先生体验了迥然不同的两种感觉。在1996年初回北京的时候,面对着自己久久思念的祖国,他居然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手足无措和慌乱,那是一种很迷惘的感觉。“我当时就怎么也没想明白,为什么原本应该很亲切和熟悉的北京,一下子却让我这样的难以适应和陌生。”黄先生在回忆当年的那种感觉时微微皱着眉头。就这样,这种手足无措几乎弥漫了呆在北京的整整两年,这两年中黄先生一直在思索产生这种陌生和排斥的原因,两年后他返回美国。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摸索,于2001年底重回北京的黄先生终于可以轻松自如地面对自己的祖国和本土文化,他终于摆脱了当年的不知所措与困窘。而那时所遭遇的一切,他现在可以很肯定地告诉我们是缘于——“重返本土文化休克”(Reverse Culture Shock)。
当然在此之前让我们先一起来了解“文化休克”这个概念。“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最早是由世界著名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 Oberg)于1960年提出来的。他把这一概念界定为“由于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又不熟悉对方的社会符号,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这种“深度焦虑症”主要表现为面临完全陌生的环境时所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是很正常的。黄先生对“文化休克”字面上的叙述让我不由得想起日前流行的一部美国电影《迷失东京》,剧里的故事就描述了一位美国演员来到东京之后所体验的种种微妙的迷失与困窘,那就像幽灵一样久久徘徊在他的心头。也许“文化休克”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难以名状的迷失。
初到美国不久的黄伟东先生就强烈地体验到了这种“文化休克”的存在。从小一直被父母师长灌输以及自己多年的教育模式所培养起来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开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于是自己因而变得脆弱,压力增大,甚至会失去应有的信心。黄先生给我们举了一个关于中国人所说的“和”的例子,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强调协调和平和,“以不变应万变”。这也是从小我们就形成的一种价值观,我们会觉得宝贵,可是来到美国之后才发现一切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你明明是对的可是又由于某些原因来强调“和气”,美国人就会认为你是软弱的和可以欺负的。黄先生就在维持这种和气的时候受到了美国学生的误解,他们都一致地认为眼前的这个中国人很好欺负,是个没有原则和主见的人。想想看,这有多么的让人委曲和难受。另外,美国人还非常强调个人权力与个人英雄主义,就像是美国电影里常常表达的那样,往往都是一个英雄神奇般地改变和扭转了一切,创造了奇迹。
其实归根结底,这一切冲击和矛盾都来自于美国和中国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美国文化是以基督教为利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中国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如果说美国是一种个体主义取向的文化,那么中国就是一种以种群主义取向的文化。黄先生将这种“文化休克”的原因归结到文化学角度时认为,由于原有文化的模式在母国里一直根深蒂固,于是当一个人面临一种新的异质文化的时候,如果他还是简单以原有文化作为认识和批判现有现象和行为准则的时候,就势必会产生这种“文化休克”。当然除了单纯的文化原因外也有更广泛的社会学因素,比如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等等。在中国,人们往往最先看见的是人,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可在美国你最先见到的是车,尤其在美国的中小城市,很少会有高楼大厦和聚集在一起的人群,街上除了一些来来往往的小汽车外几乎没有人在走动,连找个问路的人都很困难。习惯在中国大都市生活的人在来到美国之后都会产生一种视角反差,当然对于那些习惯在热闹场景和浓浓的人际关系中生活的中国人来说,这样陌生的环境的确也是有点为难。
于是他一直在调整和适应,慢慢地黄先生在美国居住的时间长了,最初的疏远和陌生被他一点点地用努力克服掉了,那种心理上的混乱、沮丧、孤独感、失落感也随着渐渐减少,他开始慢慢地适应了美国这种异文化的环境。可是就在这时他突然返回了北京,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1996年的那一次,想不到刚刚摆脱的那种煎熬和冲击又一次卷土重来。“于是我又被扔到油锅里煎了一次”,黄先生和我们开着玩笑,“的确,这种陌生和不适应要比上一次更为强烈,因为先前我面临的是完全陌生的国家。可是当今我面临的确是我的祖国,我从小一直生活的亲爱的祖国,这种陌生和不知所措在当时的我看来很是没来由。”
可是,黄先生现在已经知道那是“重返本土文化休克”,用英语来说就是Reverse Culture Shock。产生“重返本土文化休克”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在母国文化中原先所持的社会角色的丧失。在国外呆上一段时间,尽管你努力适应了异质文化,可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就是对于你熟悉的本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疏远。回国之后你就会慢慢发现中国已经不再是你原来所熟悉和一直想念的中国了,然后一切开始陌生和疏远。同时在国外辛辛苦苦所形成的一些价值观也必然和中国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相抵触,造成了黄先生所描述的不知所措的矛盾和冲突。“像我们这些海归,异国文化中积累和摸索出来的经验在母国文化中开始变得不灵验,这真是最让我不能忍受的地方。这种感觉让我无所适从,也影响着我在国内工作和生活中价值的正常发挥。我开始回避,开始想念着在国外生活的种种好处,可是这种想念对于我在国内的生活几乎是没有一点用处的,因为我只会更加的眼高手低和回避现实。”
摆脱煎熬:“第三文化”思维的锻造
那么现在的黄先生呢? 当然早已摆脱了当年的“文化休克”和“重返本土文化休克”。经过了这么多年反反复复的煎熬和冲击,他开始慢慢摸索出一条路来,一种特别适合那些经历了出国回国的人们的灵丹妙药,那就是——“第三文化”思维。我们可以先从世界著名教育专家佩利(William Perry)的理论中获得启发,即一个人要跨越自己本土文化的思维局限,一般需要通过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二元思维(Dualism Thinking)阶段,这一阶段的人在任何场合看世界都是好坏分明,黑白清楚,判断的标准一般仅仅依赖于外部权威。其实许多人一辈子都在这种二元思维中挣扎,他们一般说来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节,基本上都会信仰宗教,他们不想也不愿意接受与己相反的观点;
第二个阶段是多元性思维(Multiplicity Thinking)阶段,具备多元性思维的人往往喜欢挑战外部权威,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有不同的标准,于是对一个问题也应该从多方面去考虑。但是,该阶段思维的人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些差别,也没有建立自己和外部差距之间的关系,态度上比较消极。通常情况下还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那又怎么样,反正是多种标准,怎么样都行”的态度,在行为上往往还会受自己二元思维的影响;
第三个阶段是情景相对思维(Contextual Relativism Thinking)阶段,拥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一般能根据特定的情景和场合,收集尽量充分的信息并做出判断。他们了解自己和外部的差异,视自己的决定和判断为多方面的整合,但同时他们也对自己整合的观点缺乏坚持的决心;
第四个阶段就是坚持相对性思维(Committed Relativism Thinking)阶段,处于此阶段的人在做决定时往往能够超越自己本土文化的限制,他们经常会根据几种价值观来判断,并在特定的情景和场合下选择最适合自身利益的决定并予以坚持。他们的重点在于决策过程,而不是去迎合某种“可接受”的结果。但在决策过程中,他们往往因为巨大的压力又回到自己熟悉的文化中,并习惯性地运用二元思维来做决定。可是同时他们一旦决策完成,就会对最终的决定坚持不懈。
黄先生简单地解释了这四个阶段,然后向我们提出了“第三文化”的概念。建立“第三文化”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文化思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对新的环境和新的文化时努力收集信息,在做决策的过程中追求特定的情景和场合下最合适的选择,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区别于自己的母国文化和所在国文化,属于多少有些虚拟的文化,于是我们就称其为“第三文化”。具体来说,我们首先要依据自己所在的本土文化,运用二元思维的方式建立起自己始终坚信的核心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也就是你要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这个问题,你要知道自己的底线是哪些,哪些是自己愿意坚持不懈地固守的准则。那么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你必须坚持的就是你是一个中国人。“像我自己,我会很愿意让我身边的朋友和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很中国人的中国人,于是他们就会因此确定我的身份并对我之后的行为准则有相应的期待。”说到这里,黄先生对那样一些人表示了鄙夷和不屑,他们明明是中国人却又时时刻刻都标榜着自己生活在似乎天堂一样的美国,任何时候都把英语挂在嘴边,似乎他不讲英语人家就不知道他实在是会说英语一样。而且还用美国人所尊崇的所有的行为准则来行事,好像巴不得立马就放弃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这样做其实很没有必要,你明明就是一个中国人,你最要坚持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这一点,你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然后别人才会对你产生相应的期待。像他们这样,中国人会不愿意理睬你,而外国人也会对你的身份取向很迷惑,有时还会瞧不起你。而必须要知道的是,你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那么接着看关于“第三文化”思维的锻造,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些底线性质的核心价值,然后就在这个基础上运用相对思维来建立更大的思维模式。当然可以有选择地放弃一些自己本土文化里的价值观和准则来适应不同的文化背景,建立超越自己传统文化同时又不拘泥于所在地文化的“第三文化”。在出现“重返本土文化休克”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建立这种“第三文化”的思维,应努力在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和自己所在异国文化所形成的价值观之间来进行反复地权衡,并根据特定的情景和场合选择最适合自身利益的决定,做到在任何文化环境中都可以轻松自如。谈到这种“第三文化”的时候,黄伟东先生显得格外的自豪,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黄先生的确在跨文化沟通中做到了游刃有余,当初那种难以名状的煎熬俨然全都成为经验积累的财富。
教你最短时间之内“跨文化”
采访进行了将近一半,黄先生终于从“文化休克”和“重返本土文化休克”的迷失和煎熬中走出来,更加自如地向我们指点跨文化中的迷津。“你相信吗? 我可以在最短时间里教会你怎样跨文化,也就需要三个小时左右。”
黄先生的三个小时主要集中在了三个问题上,当然这三个问题之间没有什么平均分配时间的意思。黄先生认为对于那些并不是很了解什么是“跨文化”或者是不知道如何“跨文化”的人,如果这三个问题让他们弄明白的话,也就基本上可以很自然地掌握 “跨文化”了。那就是不同文化中自然和人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文化对于文化本身的理解。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自然和人的关系,这是所有文化都必然要面临的问题,可是不同文化对待自然和人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也会因此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种关系。在中国的文化中,我们一直追求的是自然与人的和谐,强调“天人合一”。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代表了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以“外部为中心”的文化观念。我们会愿意相信是许多外部因素左右着我们的命运,于是在行为上就表现为,尽管是个人取得了成就,可往往也会强调外部因素。当然如果有什么事做错了在潜意识里也会自然而然地归结到外部因素上去,很多时候这种归结表现成一种推脱的“借口”。中国有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鲜明体现了这种“外部中心”的想法。可是在大部分受过基督教文化熏陶的国家里,以美国作为典型代表,他们会认为“人定胜天”,人是可以控制并决定自然的,这是一种以“内部为中心”的文化。在这样一种文化里,人们往往会觉得是由自己掌握着自己的命运,那么在行为上也会自己对自己负责,就算是犯了错,也会自己主动承认,努力承担结果并尽力做出弥补。
那么再来看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文化里,由于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也随着不一样。这里我们要分析人际间的种种关系,如人情与任务的轻重,人情和法律的关系,上级与下级关系、父子关系、夫妻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等等。在不同的文化里,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由此不同。黄先生先是给我们举了上下级关系的例子,“在中国,如果一个老板让自己的下属周末帮忙去搬家的话,有95%的中国下属会很愿意这样无偿地帮助自己的老板。可是换成在美国的话,会有几乎相同比例甚至大于这个比例的人拒绝这样做。他们会很自然地回答:We are nothing but I just work for you. 言外之意就是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的,我没有必要在私人时间里去无偿帮助你。”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文化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等。下属对于上司的期待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北美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地解决工作中遇见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我们只有了解了这种不同的想法,才可以做到在不同文化的工作中保持一种专有身份的准确无误地确认,同样也给予对方以合适的期待,只有这样的话才有可能进行之间的工作沟通并建立信任以及维持这种信任。其实除此之外的其他人际关系也是一样,我们要先了解不同角色的人们之间通常是怎样进行交往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协调好自己的角色。当我们知道自己在这种文化中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上时,就会调整行为模式,并对与自己交往的人预先产生一种适宜的角色期待,这样在彼此真正交往的时候就会避免不必要的分歧、误解和冲突,也会更有效地建立信任。
最后更大份量的问题都集中在对文化的不同理解上面。“文化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你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说明白到底什么是文化,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
什么是文化?黄伟东先生在这里很生动地给我们打了“洋葱”的比喻,这是根据世界著名的跨文化专家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关于文化的解析。“文化就像是一个洋葱,有很多很多层。”最外表的一层称象征物(Symbols),如服装、语言、建筑物等等,这是人的肉眼所能看见的,也是很容易看出来的;第二层是英雄人物性格(Heroes),在一种文化里,人们所崇拜英雄的性格也就多多少少地代表了此文化里大多数人的性格,因此我们了解英雄的性格,很大程度上也就了解英雄所在的文化的民族性格;第三层是礼仪(Rituals),礼仪是每种文化里的对人和自然独特的表示方式,比如在中国文化里,主要场合吃饭时的位置安排,很有讲究。日本人的鞠躬和进门脱鞋等等;最里的一层是也就是最核心的一层是价值观(Values),指的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些标准会因文化不一样而绝然不同。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邃和难以理解的部分,它是文化的基石。其与空气一般,我们每天都在其中,可又没意识到其的存在。不同文化对世界和自然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些会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我需要知道的是,文化是没有好与坏之分的,只有彼此之间的不同,培养接受和尊重不同文化的意识,才是掌握跨文化沟通技能的良好开始。
“当然对文化的不同理解,这是个很庞大和复杂的问题,即使用上三天两夜恐怕也难以尽述”,他笑着说,“可是关于上面这三个问题,如果在面临不同文化的时候,你都可以记在心里并且在适当时候运用的话。那么很幸运,你已经掌握初步进行跨文化的技巧了,至少你会避免不同文化沟通中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
这里关于不同文化的理解上,黄先生有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不久前他在给外国人讲课的时候,用一张很简单的图画向这些老外展示了什么是中国人的典型思维。“这张画很简单就可以画成”,黄先生描述着,“它是很典型的中国田园生活的情景,首先有一座山,山下有一些梯田,梯田下又有一些农户的小房屋。旁边会有一条灌溉着梯田的小河在流淌着。那么现在你来想想看什么是对于这些农户最重要的?”我最先想出来的是梯田,黄先生笑着说,“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你再来想想什么对梯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山? 哦不!是水!”“没错,是水,就是那条灌溉着梯田的小河。它才最重要。”
黄先生一点点更形象地加以解释。在典型的中国思维中,小河下游的农户会千方百计地和上游的农户搞好关系,因为他们知道上面的水对于他们的生存有多么的重要,于是掌握着最上面水源的人就成为最有权力的人。这“水”当然并不只是单纯的“水”,而是象征了一种资源,这张画很简单地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社会的运作方式。在这种文化里,谁站在“水”的最上面,谁手里掌握着最丰富的资源,谁就是最有权力的人。在此之下的人就会拼命地和他上面的有权力的人搞好关系,因为只要这样才可以更快更方便地办好自己的事。“可是当我询问那些老外,如果他们处在小河的下游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办。天知道他们居然给出了很不一样的答案,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提到需要上游的人保持好关系。有的提出要立法,因为水是大家的公共财产,不可以被最上面的人占据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也有的人想到要打倒最上面的人,然后自己住到水的上游去。”这个简单的小图画以及不同文化的人产生的不同行为取向,很鲜明地让我们看出了文化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的差异,也很好地给一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以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感悟。他们会惊讶,原来中国人是这样想的啊。
3R模式: 当中国文化“遭遇”跨文化
在当前全球化的趋势下,一些非常传统的中国文化思维开始面临了挑战和困惑。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国本土文化的核心是哪些,总结看有哪些准则和价值观是五千年一直没有改变,而且在将来似乎也不会改变的,然后接着分析在这些没有改变的准则中有哪些会成为中国走向国际化的障碍。于是,克服并调整这些准则就成为我们现在进行跨文化沟通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所以每个人在进行跨文化沟通时,先想想这些问题,然后找出自己的答案来解决问题才是有效的。
认识跨文化中的文化差异并协调这种文化差异也是很重要的。这里黄先生向我们介绍了“高情景沟通”和“低情景沟通”的概念。情景是某个给定的沟通过程中数量信息的总称,包括沟通过程中的有声和无声方面。在非语言沟通中,情景的非语言方面就成为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如眼神、表情、手势、动作、亲近方式和空间的使用等等。任何文化中,情景部分在沟通中的比例越大,人们互相接受和传递信息就越困难。在低情景化的沟通中,信息是通过语言来传递的,因此理解比高情景化的沟通要容易得多。像美国就属于低情景文化,多运用低情景沟通,此外还有盎格鲁文化、日耳曼文化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国家;而日本、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以及俄罗斯和阿拉伯的一些国家属于高情景文化,运用的是高情景沟通。搞清楚这个区别就可以在相应的文化沟通中避免不必要的尴尬。
另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国际化的趋势的时候,尊重其他文化也是必须的。尽管每个文化的人都会这样的倾向,就是觉得自己的文化才是最好的、最文明的和最优秀的,其它文化都不如自己的好,可是我们要知道文化本来没有好和坏之分,只有不同之别。就如帕斯卡(Blaise Pasca)在其《感想录》所说的名句“在比利牛斯山(Pyrenees Mountain)这边是真理的东西,在比利牛斯山那边就成了谬误。”培养接受和尊重不同文化的意识,摒弃文化中的偏见是掌握拓展我们的视野良好开始,同时,我们也由此了解对方对我们所持的期望。
上面所说的当中国文化面临跨文化时要注意的三个方面被黄先生总结为3R模式,也就是认识文化差异(Recognize Cultural Difference)、尊重其它文化(Respect Cultural Difference)以及协同文化差异(Reconcile Cultural Difference)。
打造属于你自己的“跨文化工具箱”
“跨文化工具箱”是黄伟东先生在跨文化中提出来的最形象的概念。他认为,每个人在进行跨文化沟通的过程中,都要不断地打造属于自己的“工具箱”。这个小箱子的核心是你自己本土文化的价值观,然后随着感受不同文化的经历,你就把与之相适应的更多的“文化工具”放进去,这样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很自如地马上调用不同的“工具”。黄先生和我们开着玩笑,“就像是说你遇见了一个德国的螺丝扣,可是你却拼命地用中国螺丝扣专用的工具去卸它,根本就是无济于事的。你的工具箱里必须要有德国专用的钳子。”于是在遇见了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的时候,黄先生就拿出他的“工具箱”里与之相匹配的工具,一切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黄先生强调,跨国经营的企业经理人更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工具箱”。一个企业跨出国界经营,要实现商业目标必须融合三种文化——自己国家的文化、目标市场国家的文化、企业的文化,执行这项任务的当然是企业的国际经理人。国际经理人必须建立更大的文化核心,这个文化核心要像一个“工具箱”,自己清楚知道箱里最重要的工具是什么,接着,不断添置新的工具。比如自己是中国人,就应该清楚作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文化工具是什么。然后,根据需要,不断添置“美国文化”、“日本文化”、“德国文化”等工具以充实自己的工具箱。当面临不同文化的人以及不同文化下管理的时候,马上能调用不同的文化工具,做到无论遇见任何文化难题,都能使用自己的工具解决 。对国际经理人来说既要掌握公司的原则性文化,又要根据不同的情景做出判断适应本土的具体情况,最难的就是有机地平衡普遍性和灵活性。要知道做到这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管理者一生追求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国企业要成功跨国经营,就要不断打造自己企业经理人的文化工具箱。
结语
对于黄伟东先生的采访是异常轻松而且受益菲浅的,当黄先生从当年“文化休克”和“重返本土文化休克”的煎熬和痛苦中,向我展示着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点点在跨文化中摸索出来的经验的时候,他变得欣慰。的确,这是一个成功的行走者,在跨文化中一边行走一边实践,在煎熬和冲击中受到了洗礼,取得了今天的非凡成就。所以说,煎熬也许是痛苦的,可是在煎熬中收获到属于你自己的财富确是让人欣喜的。
黄伟东先生就这样一直行走在跨文化中,且煎熬且收获。